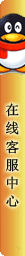绝大多数在职的记者,甚至是那些跑政治口的记者都还没有坐下来采访过美国总统,但 2015 年 1 月,三位 YouTube 红人得到了这样一次机会。他们问了关于掉进白宫的无人机、网络中立的问题,还问了总统他希望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然后 GloZell Green(拥有 300 万粉丝)向这位美国总统递了一支她标志性的绿色唇膏。“这是送给第一夫人的,”她说。奥巴马有些不知所措。“你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吗?”他说。

题图为奥巴马总统和丹·菲佛(中)以及负责战略沟通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下)开玩笑。图片来自白宫。
即将离职的丹·菲佛(Dan Pfeiffer)是总统的高级顾问,负责白宫的公关工作。在他看来,像刚才那样的尴尬时刻正是总统的部分魅力所在:总统的真情流露有时候倒会帮助这位离人们很远的大国首脑贴近他庞大的支持者群体。自奥巴马第一次竞选总统以来,菲佛就是他的幕僚;在扩展他的老板和美国人民交流的平台方面,他算是其中的关键人物。让习惯了安排专访的白宫新闻团队懊恼的是,总统和扎克·加利费安纳基斯(Zach Galifianakis)在搞笑网站 Funny or Die 上开玩笑、宣传他的医疗保障计划、和地方天气预报主持人聊天气,还在一个 Buzzfeed 上的视频里对着镜子做鬼脸。白宫在 Facebook、Twitter 和 Medium(没错,就是本网站)上也搞得风生水起。白宫还打破常规,在总统发布国情咨文之前,就把全文放在了 Medium 上。
就在菲佛从白宫卸任前夜,他同意和 Backchannel 聊聊他主持下的白宫公关策略,分享他对当前和未来政治媒体状况的看法。他最让人惊讶的预言是:未来的白宫将生产出自己的内容,这无疑将让地位已经下降的传统媒体文人雅士们发出了更大的哀嚎。
考虑到叙述清楚和文章长度,采访内容有所删节。
Steven Levy:你主管白宫公关工作期间,最具标志性的事情之一就是总统出现在了“非传统的”传播渠道里。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你又是如何实施这个计划的?
丹·菲佛:我参与了 2008 年的总统竞选,而且我们想出了创新的办法来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这让我们很自豪。后来我们入驻白宫,发现那儿的传播手段还很古老。由于信息安全的原因,我们都不能上社交媒体,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调整了思路,把数字战略整合进了白宫。我们意识到,在这个媒体原子化的时代,人们有很多信息渠道可以选择,你不能只是依靠老旧的主流沟通工具来接近公众,这也是我们在总统竞选的过程中学到的。所以在最开始的几年里,我们还是做的传统的工作,但同时也进行了一次 Facebook 上的聊天,还尝试着做了许多网络内容。
在 2012 年中期选举之后,形势变化加剧,我们以前的做法都不足以按照期望的那样把信息传达给公众了。传统媒体的渗透力正在被明显削弱。我们想向外传递的信息都传达不出去,而与此同时,由于社交媒体的强大,其他人向别人传达的关于我们的信息却纷纷到了公众的耳朵里。所以我们尝试了一种“意面策略”——把很多东西朝墙上扔去,看最后什么能粘在上面不掉下来,也就是做各种尝试,看最后哪个管用。而且我们还非常乐意去承担风险,而这在过去传统的政治规则下是不可能去承担的。


BuzzFeed 上的奥巴马 GIF 动图
在你最初做出的数字化努力中,比如让奥巴马在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上的亮相,用的似乎还是传统媒体的语言和语法。但一段时间以后,你采用了这些新传播渠道的语言模式。
没错。最初的时候,我们会把与马克·扎克伯格在 Facebook 的访谈和《60 分钟》史蒂夫·克罗夫特的访谈一样看待。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根据访谈发生的地方调整一下(对待它的策略)。在中期选举之后,总统指示我们要加大力度,尝试采用更创新、更积极的手段。他的看法是:当你在思想要如何在数字空间里公关的时候,就注定要打这场大仗,因为真实性是在数字空间的基础。但在政治界,纪律是立足的根本。有时候,这两者会造成一些对立。所以我们决定再冒一个险。Buzzfeed 就是个绝好的例子。我们当时知道,Buzzfeed 上的视频深受其用户和社交媒体的喜爱,但这却会招致来自一些行家和媒体评论家的许多批评。
说说他们都批评了些什么。
批评太多了,说我们想出来这些自以为是的点子,为的就是尽可能避免去和白宫的正式报道团队对话。实际上这并不是我们的策略。这不是个非此即彼的策略,而是两方面兼顾。
你们的策略和尼克松上《Laugh In》或者克林顿上《Arsenio Hall》吹萨克斯有什么区别?
从某种角度上讲没有区别。任何一位政治家都总会寻找展示真实自我、真实性情的方式。不同的是,我们想要面对的受众是聚集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的特定人群,而且要用他们喜欢听的方式向他们表达。如果我们和时政网站 Vox 做一次采访,就要做一个以政策方面的问题细节为主的采访,这是 Vox 的读者想看的东西。Buzzfeed 又有它自己的特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和本·史密斯(Ben Smith)有一个严肃的访谈,但同时也配了一个搞笑的视频,因为那才是他们想看的东西。
对白宫来说,媒体的这种分化带来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你不能再想只用一个全国电视讲话,就能让 1.5 亿人都听到你说什么。所以你必须付出比从前的总统多 15、20、30 倍的努力,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但好的一面是,你可以(直接)跟公众说话。在拥有所有这些不同的传播渠道之前,华盛顿的新闻团队可以决定那天的话题是什么。就拿埃博拉打比方吧——它会放在所有新闻的前面,也应该放在前面,因为它是个大事。但我们不想只谈埃博拉,还想传递关于医保的信息,因为我们正在为医保注册季做准备。10 年前,我们没有真正的渠道来说这些,但现在,总统可以回答一堆关于埃博拉的问题,而我们也能为 WebMD(美国最大的医疗健康服务网站)的用户们准备好和医保相关的内容。

奥巴马参加网络视频节目《Between Two Ferns》
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效果,有什么指标可以说明吗?
有的。在 Funny or Die 网站上总统和《Between Two Ferns》的加利费安纳基斯对话的视频下面有一个注册医保的申请链接,而它让很多人都顺着链接填写了申请表格。Buzzfeed 上的那则视频也让很多人从 Facebook 上直接点到了 Healthcare.gov 上。
这两个视频都表示总统还真是愿意尝试不同的事物。你的建议有被他拒绝过,因为要他做的事不够“总统范儿”吗?
像这样的提议,通常我们都会在最后呈递到他那儿之前认真做好筛选工作。以《Between Two Ferns》的视频为例,由于一开始 healthcare.gov 那个网站出了点儿问题,我们当时其实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所以我们一直在念叨着“万福玛丽亚”。但这是个需要胆量的事,而我们愿意去尝试那些华盛顿的一些人会说没有总统范儿的事。我一直认为,人们想要时不时看到自己的总统不那么严肃的样子。他很会把握开玩笑的时机,所以在这些视频里,他都表现得非常好。
你刚才说到了真实的重要性。当人们第一次看到这类视频的时候会说:“哇,这个也太大胆了吧。”但当看到第五、第六个类似视频的时候,看着总统做一些人们觉得总统不会做的事,就没那么有震撼性了。那你觉得到了什么程度,真实的东西会变成具有表演性质?
那正是我们要堤防的情况。我们做的所有事,即使是不好笑的事情,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要你把同样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但我们在白宫里总是会提醒自己,我们是唯一一群看到总统所做的一切的人。如果你去看 ESPN 观众、我们在 Facebook 上的观众和媒体受众这三个群体所形成的维恩图(Venn diagrams,一种用来显示元素集合重叠区域的图示),你会发现并不会有很多人在两个不同的渠道上看到过他,更别说同时在三个渠道上都见过他的了。所以他总是会觉得,在我们这些本职工作就是看他的人面前,他自己有点儿曝光过度了,但其实只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比一般公众看他看得多一些。
我觉得你让总统去和 YouTube 红人见面,是不是为了追求新奇而硬生生安排的。
我们很擅长找《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和他聊聊我们的气候计划。但网络红人的粉丝们也很重要,我们也想去接触他们的粉丝——YouTube 上的红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当时知道这肯定会招致传统的华盛顿记者们的批评,他们会说,那些人问的都是些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但(这些 YouTube 红人们问的)都是他们的受众想听的问题,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受欢迎啊。这些视频并不是为了代替白宫新闻发布会或者主流媒体记者的采访,而只是另一种接近受众的尝试。

奥巴马和 YouTube 红人 GloZell Green 聊天
你曾经打破常规,提前在 Medium 上发布了国情咨文的讲稿。这在白宫内部有过争论吗?
在白宫里有过些微的争论。任何时候你拿着一个守了几十年的规矩,在最后一刻说:我想不这么干了,人们是会心里有点儿不舒服。但当我们解释清楚我们的逻辑以后,大家就都和我们一条心了。我个人认为,这个不准刊登国情咨文的禁令其实是场闹剧。以我的经验,白宫会在国情咨文演讲开始前 20 到 30 分钟的时候,取消禁止刊登的禁令,随后记者们就能把它用电邮发给他们在华盛顿的消息源,然后他们的消息源再把电邮转给他们的朋友,最后在演讲结束之前,华盛顿的所有人都有机会看到这份材料,而公众却只能听总统讲完。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华盛顿的人能看到这份材料,为什么公众不能看?把这份文件放到一个人们会去看较长的内容的地方,意义可太大了。我们觉得人们都很好地接收到了这些信息,而且我想(换了其他人)也会这么做的。就在发表出来几天之后,密特·罗姆尼宣布他将不再参选总统,而他也把这份声明发在了 Medium 上。
好吧,在我看来,所有人都应该一直在 Medium 上发东西。
那是肯定的。我是说,这才是你我这场谈话的要点所在。(确实,在菲佛在任的最后一天,他也把他的辞职信贴在了 Medium 上。)
我听说,为了听取关于如何和受众交流的建议,你曾经拜访过一些硅谷领袖。你都和谁聊过?你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什么呢?
我不想说得太具体,因为我请所有这些人都对我们的谈话保密。但我们和所有大平台的人都聊过,还和在纽约和硅谷做数字参与和营销的人、以及风投界的人聊过,请他们帮我们想一想接下来会有哪些相关的技术出现。这个项目的目标之一,就是确保我们不要自以为已经为 2016 年 3 月的选举制定了完美的策略和措施的时候,却在半年后发现冒出了三个新的情况。现在的舆论环境充满了变数。
他们向我们强调了几件事情。当我解释我们面临的公关挑战时,许多人说:“是啊,真的好难。”所以不是只有我们难,所有人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和我会面的人里,没人给出什么神奇的答案。
第二件事涉及到借助数字世界里有影响力的人,来提升我们的工作成效。然后第三个问题关于真实性的必要性。这不只是说总统要保证真实,而是说所有有网络账户或者在网上有追随者的行政官员都要真实表现自己。你的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需要说一些比重复奥巴马说过的话更真实的东西。它必须成为一种真正的用来接触民众的策略,比如要和公众有来有往地对话、回应那些不同意你的人,或者发言感谢说得很好的人,或者把他们的推文加入最喜欢的推文收藏夹(这个收藏夹是公开的,谁都可以看到,译注)。对于在政府工作的人来说,这么做没那么容易,因为他们的正职并不是做这个。而且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因为作为一个在白宫或者在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你的目标是不要让自己上报纸头条,而是不要招来你不需要的关注。
你怎么展望白宫未来的公关工作呢——你觉得到 2020 年的时候,情况会是怎样?
白宫官员更大的职责,将是通过网络接触公众。如果你在白宫做和气候变化政策相关的工作,你不会每周和环保团体开 N 个会,而是花时间在 Twitter、Facebook 或者任何一个下一代的社交平台上,和那些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开展交流。你将不会像以前做大型广播电视采访那样接触到那么多的公众,但交流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和你交流的都是些对相关事物非常投入的人,他们可以为了你所关注的事情的利益而实实在在地去行动。
而且我想——这可能有点微妙——白宫将必须掌握更多的资源来投入生产内容。我们有很多写文字材料的人——讲话、话题文章、新闻发布会通稿等等——但我们还需要一些通过视觉、图形以及视频媒介的人来传递同样的信息。这事儿有点微妙是因为,你不想把它做成政治宣传(propaganda)。你必须对此进行仔细的审查,但公众对于此类内容的需求又是非常大的。传统的新闻渠道不具备 24/7 全天候生产互联网所需的如此大量内容的资源。
有个事情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发布一个新闻发布会通稿,它会被人们认为这才是总统开展交流的正确方式。但如果我们发布一个视频,它就会被视为宣传。这种心态以后得改一改,(人们得认识到)视频只是一种更容易分享、更有趣的交流方式,它说的内容和新闻发布会通稿是一样的。所有人都得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你能举一个你非传统的沟通方式没有奏效的例子吗?
有一些事情做的确实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几周前,我们做了个视频在 Facebook 上宣传平价医疗法案注册人数,想把更多的信息直接放到数字平台上去。视频本身的效果还不错,有几百万的访问量,但这个表现却不如近期的其他内容。我想我疏漏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平价医疗法案注册人数是否达到了某一特定数量,是报道白宫的记者们热议的话题,但对于上 Facebook 的人来说,没人对这个问题真有太大的好奇心。
也许你需要给它配个更好的标题。
(笑)是啊。比如“你之所以不会相信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的 10 大理由!”但我们吸取的很重要的经验是,虽然媒体对注册人数是 1000 万还是 1100 万非常感兴趣,但对公众来说,这真没什么关系。
最后一个和你离开白宫有关的问题。既然前一任白宫新闻发言人杰伊·卡尼(Jay Carney)后来去了亚马逊担任公关主管,那你又将去哪家硅谷公司工作呢?
我的首要任务是去休个长假。
这是客套话。
这是真的。我不知道我下一步想做什么。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白宫工作,或者在努力想进白宫工作,所以离开白宫之后,我算是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我很好奇,想看看是不是有办法在现在这样的媒体环境里继续探索如何成功扩散信息,不管是去一家公司还是做几个项目还是怎么样,这都是我的目的。至于我是真的会参与其中,还是说我只是站在一边做个旁观者,这都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