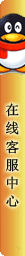人物:徐俊
职务:杜邦(中国)公共事务总监
(徐俊人如其名,有种如沐春风的温和,谦逊有礼的他非常有江南书生的感觉,看着他谈话,你会觉得对面意态优雅,微笑不断的他越看越耐看。公关行业是一件非常辛苦的职业,但徐俊却做得很快乐。)
除夕之夜入公关
少年时期的职业理想和公关并无关联。高二那年,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的倡导下,“北京中日青年友好之船”代表团去日本考察交流,我幸运地成为其中的高中生团员之一。第一次的日本之行让我萌生了做外交工作的愿望,我的理想来得非常偶然,但一来就非常强烈。因为这个理想,在预招老师的指导下,我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只填了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就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新闻系。
在大学里我首次和公关结缘,最初是参与郭惠民老师的原版公关书籍的中文翻译工作,后来在学校记者团的编制下我组建了首届校学生公关协会,并且还请校外的老师和从业人员来做讲座搞公关培训,搞得有声有色。尽管如此,当时我还是一心想做驻外记者。可是毕业那年是1990年,当时新闻界正好内部调整,因此没机会进新闻单位。我进入了北京广告公司做客户服务,经过两年的磨砺,当时觉得广告这一行我都学会了。
于是,年少气盛的我离开北广,去一家香港广告公司负责业务。公司规模的悬殊差异让我很快就意识到业务拓展的困难,也发现我并没有完全懂得这个行业。两年半的时间是不可能懂得一个行业的,起码需要五年吧。
(徐俊主动辞职,辞职后的他并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刚刚工作两年半就待业在家,这可是在90年代初期大家都讲究铁饭碗的时候,当时徐俊的父母很为一向引以为自豪的儿子担心。而徐俊自己从中吸取了经验,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浮躁。)
机遇的来临很偶然,但抓住机遇的人肯定都有着必然吧。那时,刚进入中国的博雅公关在北京招人。北京公关圈里的人推荐了我。我至今记得面试,1992年大年三十的下午,在三三两两的爆竹辞旧声中带点激动带点兴奋也带点不安第一次踏进博雅中国公司的大门,坐在老板——一位和我同岁的英国女性面前。
她问我觉得自己适合公关这个工作吗?我说我这个人比较缺乏创意,比如想一个很好的广告语等,这不是我的强项。她说那你会不会学习?我说我读了十几年的书,学习应该会吧。她说,学习是在合适的时间找到合适的人去问合适的问题,她说公关是一个团队活动,你要知道找谁帮忙你,这是最起码的素质。我说我这个还是可以的。那次面试给我的启发很大,就是公关不是靠个人,而是靠团队。
就这样,1992年的除夕夜,我入了公关这一行。
(说起16年前的往事,徐俊记忆犹新。他深有感触地说年轻人在大学里要多多走出校园,多些社会实践,和社会多些互动,无意中多看一眼,多听一句话,多学一门课,多识一个人,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帮助。刻意为之,反而不见得如愿以偿。)
十年博雅渐长成
(公关从业人员流动性很大。徐俊却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人,从事公关工作至今16年,其中在博雅一干就是十年。)
我很感谢博雅。十年的博雅生涯让我成为一个公关人。
博雅的国际网络让我得益不少。在博雅的10年,我换了不少地方,从北京到香港,到上海、新加坡、澳大利亚,再回到上海;而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也从开始的企业传播拓展到了市场传播的领域。
一进博雅,我就感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准确把握交流的挑战。学国际新闻的时候,我学过新闻写作,英语的运用也是必须的课程,但一到博雅,就感受到语言的压力。作为一个国际化的传播者,老板对我们的用语规范相当严格。当时每写完一封英语电子邮件,都先打印一份送到老板办公室。老外则拿着红笔,逐字逐句的推敲,不一会,纸上就写满了红色的修改和批注。有一次,老板为了一个单词特意在公司里贴公告:“媒体关系”中的“媒体”一词,以前都用press,但今后要改成media。因为press指的是印刷媒体,不能准确描述当今科技手段日新月异的媒体环境。就是这样的“改作文”帮助我理解和注意中西方在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沟通环节上的诸多不同。
(虽然,徐俊交上去的文件上红色的批改还是有,但老板也看到他有培养的潜力。不久,公司派他前往博雅设于香港的分公司工作。)
香港的经历让我眼界打开。90年代中期的香港公关业已很是成熟,专业公司的分工已经细化,目标群体非常明晰,有专门负责企业上市的,有专门负责政府公关的,有专门负责奢侈品传播的等等。而当地的媒体也林林总总,定位非常明确,有产经媒体、生活休闲周刊,有区域性英文报刊也有用粤语风格写作的当地报章。不同的客户需求、纷杂的舆论环境,而术也有专攻的公关人就是其中的精准联线。
博雅提升了我对公关的认识。公关不是追求媒体的发稿量,而是追求有效的企业认知管理。认知管理可以理解为兵法里所讲究的“攻心为上”,是一种“攻心”的艺术,讲究的是通过管理公众对事务、企业或者个人的看法和理解,进而获取他们的认同,最终影响他们的行为和决策。这帮助我理解了公共关系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战略价值所在。
后来博雅又把我送到新加坡、澳大利亚,边工作边培养。走了不少地方,看似一直在博雅一家公司的我,事实上一直在不断地换城市,在一个国际公关圈里换点,这样使得不断充实的我也对公关一直充满新鲜的激情。
做公关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客户,但我一直做得很快乐。没有人会愿意看到一脸怨气的合作者。自己高兴,别人也会感染着我的快乐,快乐的沟通也是最有成效的。而且公关虽然是服务业,但面对客户,你不应该是服务他的仆人。你要看到他们是一群有需要的人,就好比是孩子,他们需要你的知识去答疑解惑、需要你的细致耐心去呵护、去消除他们的烦恼。这样想,你就会少一些抵触情绪、就会因为自己的被需要而快乐起来。我就是这样快乐着做我的工作,而且也快乐着客户的快乐。
(上海博雅的发展越来越好,徐俊也从经理升为总监。工作更多更杂,可是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快乐公关的理念,平实诚挚地待人处事。他每每告诫新同事,不要只看到公关的风光外表,心态要摆正,记住三点:这一行很辛苦、想出名很难、想发大财更是不可能。记住这三条,再入公关门,就少些怨气,知足常乐。这是一个现状,这行要承受很多委屈和压力,而回报就是所积累的众多经验和知识。)
杜邦六年坎坷中前行
(2002年开始,徐俊进入杜邦,从乙方成为甲方。)
要在公关公司获得成功,你常常要站在客户的角度看问题,但是我之前还没有从事过客户方的工作,于是觉得十年时间我也应该换换角色了,这样我的公关生涯会更全面,考虑的角度会更贴切。博雅十年,其中服务了杜邦八年,对杜邦很熟悉,到2002年进入杜邦似乎是个再自然不过的转换。
我没有因为到了客户端而感到轻松,反而感到责任的压力遽然增大。在公关公司,某个活动不尽如人意,你还可以有一些借口去为自己开脱。做了企业内部公关,这就是你的领域,事情不尽如人意?你可没有任何理由责怪供应商、其它部门的同事或是老板,因为,从策略到执行、从内部人员分配到服务商的使用,都是你的选择。责任非常明晰。
杜邦在2004年经历所谓的“特富龙”风波。对我个人来说,那件事让很多人知道了我,作为一个公关人那是一段难得的经历;但是对于一个企业而言,真是一个没有必要的痛苦。在美国这件事的核心是我们在生产涂料过程中的排放对于环境是否存在影响,而在国内演变为了炊具的安全问题。我们做了大量基于事实的沟通工作,但到目前,可能人们的误解和疑虑还没有完全消除吧。对于公关效果如何进行量化衡量一直是个业界的难题。我想,沟通传播是否有效最终还是要看你的努力对于业务所产生的实质影响。
这件出自美国的事情在中国产生“变异”进而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教训,因为是我们这些本土的传播从业人员没能解读好当时的公众心态和媒体兴奋点。跨国公司常说要管理本土化,为的是更切合当地的环境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而我同时看到的是,我们这些本土员工进入跨国公司后,在思维上很容易受影响,而失去了对周边环境我们与生俱来的敏感性,而变得对周边事物麻木。这对于企业发展和我们自身的职业发展都是危险的。传播要成功,就要用当地人听得懂的语言、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上去沟通。我很欣赏“90后”的一句宣言:不要和我夹杂英文讲中文。这当中传递出的是新一代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对多元文化的从容。每个地方的文化风土人情和思维方式各有差别,我们要了解所处社会的大环境。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公关就是要借事造势。抓住当前热点,分析社会热点背后的思潮,是我们公关从业人员必备的职业灵敏嗅觉。只有具备这样的能力,我们才能帮助一个组织在动态的大环境中营造一个好的经营发展环境。
(在徐俊身上,本土化特色很低调,但很执着。他在跨国公司多年至今没有起英文名字。他可以用英文从事工作,甚至写书,但在我们的交谈中,他努力不掺杂英文词。)
(今天的徐俊虽然户口还落在北京,但他已经在上海买房成家。)
我到过不少地方,但在上海已有12年了,我想,我还会继续选择上海,我心安处即故乡,上海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海纳百川的包容性越来越强,随着我对上海越来越熟悉,也越来越喜欢这个城市。我还和两个博雅的老外朋友一起用英文写了介绍上海衣食住行的书,把上海介绍给更多的外国朋友。在写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那些默默矗立的老房子背后的沧桑,很有感慨。
进杜邦六年,我基本上没有休满年假。这是不好的。如果你对团队很有信心,就能放心地去休假。如果你或多或少不放心,就说明你的团队建设和培养还没到位。我必须在这方面加强努力,给团队更多的机会,让自己明年能完完全全地休假。假期需要计划、生活也需要计划。我至少做到了和家人约定,每一个季度至少要有一次文化娱乐活动,比如说看话剧、舞台剧什么的。能张弛有度的、调节好工作和生活关系的人,是一个幸福的人。一个幸福的人很容易感恩、很容易快乐,也一定能调节好上班的情绪,这样他周边的人也就快乐了――快乐地工作、快乐地休息、快乐地生活、传播快乐。
|